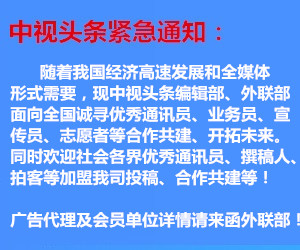1973年的巫水河畔。湘西大山深处,一所颇有几分颓废的乡村中学。周末下午的下课铃响了。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左手提了一个藤篮篮,右手提了一个自缝土布袋闪身出来,独自匆匆行走在通往“半界”的崎岖小路上。他要沿着哗哗流淌的巫水河下行几里路,争取天黑前在一个叫摆滩的地方过河,再翻上人见人怕、无比陡峭的“八十界”。山路浓荫蔽日。枝头鸟雀啁啾。那儿有对他望眼欲穿的六旬老母和他的大儿子平凡、小儿子一丁。布袋里放的是几件换洗衣服,藤篮篮里装着的则是他小儿子最爱吃的猪耳朵糖。
那一年,他应该正好43岁。林彪坠亡在蒙古温都尔汗不到两年。中国的政治天空仿佛蓦地泄过一丝希望的微光。但接着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静。大家都称呼他王教员(后来改叫王老师)。其时,王教员已打定主意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扎根落户、开花结果。家里正准备起屋呢。青苗款筹齐了,满世界找锯匠师傅。女儿亦凡(老二)很快高中毕业,马上也要下放到这里,反正同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脆和大哥、小弟做一路。兄妹仨好有个照应。老三又凡和妻子留城。看来全家以后都只能过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了。当时交通极端不便,下放地尚未通车,全家人一年最多能见上一两次面。走着走着,富于想象力的他脑海里不经意地轻轻掠过一阵旋律……他不由得悄悄哼唱起来。

没错,这个哼着小调的中年男子便是我的父亲王举信。我便是他那酷爱吃猪耳朵糖的小儿子一丁。1969年5月(也许是4月)带领奶奶和我,还有我大哥从洪江古商城鼎新街学校下放到会同农村的时候父亲刚满39岁。转眼四年了。虽因当地极缺师资而不得不让他从田间回到了三尺讲台,然返城无望,求告无门,父亲遂以其吃苦耐劳的倔强个性下定决心,打算就带领老大、老二、老四和老娘在这山旮旯里过一辈子!父亲脑子灵活,无论什么一看就会。除却语文老本行,大到英语、体育、书法的授课,小到昆虫的分类、草药的采撷辨认与临床使用,乃至糕点油条的制作工艺……唱歌、乐器、作曲更是他的强项。他在洪江放的第一颗“卫星”便是不假外求无师自通修好了解放初人民政府没收我姑姑家、“放”在市文化馆供“革命群众”使用的德国进口钢琴。我的口琴、笛子、二胡、脚踏风琴、小提琴均由父亲启蒙。前些年见到云山表兄(父亲的高足)和黔城中学健在的几位父亲过去的同事,如蔡周亮老师等;他们依旧对父亲演唱的《白毛女》中杨伯劳唱段津津乐道。

因此,《1973年的巫水河畔》,这绝非一首寻常的曲子。学校文宣队要上县里参加调演。学校领导希望长寨中学在全县脱颖而出,力拔头筹,父亲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悦耳的带有浓郁苗侗风情的曲子。依稀记得乐曲描绘了学生们采杉种、扑灭山火、邮递员送公报等劳动场面与世俗生活细节。节目的名字是什么?当时究竟排练的是表演唱还是舞剧?音乐剧?有几名演员?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真切了。只知道曲子很长,接近半小时,二胡、高胡、笛子、木鱼,几样乐器一块上。演出在县里引起了轰动。毫无悬念地斩获了演出一等奖。连县委会食堂打菜的师傅也会额外给我多打些。谁也想不到一所那么偏远的乡村中学竟能拿出这么好的节目。旋律优美、充满深情,尤具创意。惜乎几十年过去,节目不存、曲谱散佚。但9岁开始学习吹笛子的我一直对该曲目耳熟能详。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直至现在,我至少把它吹奏了几十上百遍……这首曲子犹如从父亲心田里流淌出来的一泓汩汩清泉,能够使听者的灵魂得到最大程度的慰藉。每次用竹笛吹起它,我就不自觉地想起了我那清高孤傲、任何时候都绝不向权势和厄运屈服低头,却又洁身自好、与人为善,冰雪聪明、才华横溢的父亲……想起了我们全家文革9年那段欲说还休的峥嵘岁月。


自幼习笛,我还算粗通音律吧。我感觉父亲的曲子属于那种绝对的原创,因为在任何知名和不知名的作曲家的作品中,我都不曾发现过与之有丝毫类似的旋律:东拼西凑南挪北移在当今的音乐创作之中却几乎是普遍现象!以至我们会像某音乐家调侃的那样:在闭目聆听某些音乐作品时会情不自禁地频频脱帽……缘因所邂逅的老朋友和音乐大师实在太多也!

有人说:一个家族就如同一棵根系发达的参天大树。奶奶仙逝后,身为顶梁柱的父亲无疑便处在了家族这棵大树的最末端或曰最顶端。如此,父亲一生所承受的所有阳光雨露雷鸣闪电抑或酸雨腥风尘暴雾岚则均可视之为家族茁壮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想到这一层,我对一般情况下不苟言笑的父亲便愈发肃然起敬。

2015年4月3日,命运多舛的父亲便已离开我们兄妹整整12年。我把好朋友牟迁一次偶然为我拍摄的笛子吹奏视频(约为全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发给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王瑛老师,请王瑛老师费神帮忙记谱,聊作对父亲永远的怀念。也希冀能够触发当年长寨中学文宣队的队友们如李世俐、石当全、伍东洪、黄长玉、李国贵、梁高和诸故人对往事的温馨回忆。更有意将其视为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代代传承下去,聊作子孙们未来对祖先对家族想象的历史补注。

打赏

扫码打赏,你说多少就多少








 手机版
手机版 | 艺术频道
| 艺术频道